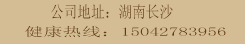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滕州市 > 滕州市资源 > 研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当前位置: 滕州市 > 滕州市资源 > 研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 当前位置: 滕州市 > 滕州市资源 > 研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当前位置: 滕州市 > 滕州市资源 > 研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在本案中原告人齐玉苓因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父女侵犯了其姓名权而进而损害其受教育的权利,符合广义定义中的请求权,因而在二审中最高法院做出了对侵犯受教育权的追究。从宪法对受教育权的保护不难发现,宪法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我们要珍惜受教育的权利,学习宪法知识,为依法治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秘书处金明甄
法院最终判给刘玉苓的10万元可能已经无法改变她的命运,但关键是宪法给了她公正,也让所有公民看到了希望。齐玉玲案跨出了这一步,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就是人民法院用宪法作为法律依据,审理案件,并且依据宪法作出了判决。加强宪法实施,这需要全社会增强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让宪法成为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准则,也让宪法与百姓能够心贴心。
——实践部章天娇
事实上,一般来讲,宪法基本权利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它给个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成为个人心理上的仰赖。如果仅仅是侵犯了她的姓名权,该案的原告可能就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上法院去告诉了,比如说,被告冒原告之名为一定的民事行为,将不会如此深切地损害原告的利益伤及原告的心灵。正因为原告的受教育权被侵害,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才这样痛恨侵权者,以至于与同乡同学母校在法庭上一次又一次地刀兵相见,可见,一审法院仅以侵犯姓名权为由进行判决是不能很好地抓住案件性质的,也是不能充分保护受害人宪法权利的,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宪法司法化的必要。
由于当下法院判案不能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如果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遭到侵害,但在其他部门法中并无具体条文加以规制,公民的权利如何得到救济呢?不可能总是以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为理由,对于侵犯以宪法条文明确加以保护的公民权利的行为置之不理吧?如果连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合理救济,又怎么能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呢?
——实践部曾维茜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该进行适用,但不能宪法私法化。宪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公法,故不应该使宪法私法化。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由民法等基本法律调整,不应让宪法介入纯属私人领域的民事争议。例如本案中宪法有关受教育权的保护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公民。
——研究部徐秋桐
宪法能够适用于私法领域。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最高地位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法律,独立存在。也正由于它的根本属性,它是一切部门法的根本,是其他法律的母法,各部门法因他应运而生,它必将兼具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
其次,宪法是统治阶级建立民主制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的国家根本法,其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主要包括了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两大方面,而保障公民权利则始终处于支配的主导地位,其调整的对象因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前两种属于宪法的公法性关系,后一种则是宪法的私法性关系,尽管宪法对于私法性关系做出的只是原则上的调整,但由此宪法的司法性属性已经不容置疑。
——秘书处赵歆然
在法理学导论课堂上第一次听老师分析这个案例,或许是因为当时刚刚才接触法学,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深刻,并没有试图深入理解这个案件背后的宪法司法化等一些列问题。直到在宪法课堂再一次与老师同学探讨,才开始深思齐玉玲案所反映出来的我国司法中的不足与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的问题。
在这个案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法院是否支持齐玉玲是否支持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却在民法通则中没有提到的受教育的权利。我认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该被实施,没有司法化也就意味着与社会大众脱节,法院判案子不能用宪法,那么,公民宪法权利被侵犯,该如何得到救济?如果宪法不能司法化,那么,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保护公民利益的意义何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国应该参照其他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比如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方案,让宪法真正融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使宪法真正意义上保护公民的权利。
——实践部古丽尼尕
宪法司法化是可行且有必要的。在实践层面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的诸多国家均早己开始了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并且实践证明效果良好,尽管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但与其他国家依然具有一定的共性,既然宪法司法化在其他国家能够有效实施,那么它在我国也一定行的通。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然而它在我国的实施仍然存在不少的困难。比如,宪法是母法,概括度高并且相当简略,对各种行为一般仅限于定性评判,太多裁量空间,难以把握裁判尺度。
——实践部金羿
我觉得此案并不可以作为宪法司法化的有力论据,这只是处理突发纠纷的权宜之策。法律援引宪法与宪法司法化也是两个概念,本案只是依据宪法判定齐玉苓的受教育权受侵犯,而并没有根据宪法处理其赔偿数额,况且宪法里也没有具体提到,所以只能判断其是援引宪法。另外,此案援引宪法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可以推进相关部门法,如教育法的进程,更好的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
——研究部蒋静漪
此案件经过二审后才彻底解决,说明中级法院没能充分利用现场证据,也没能充分听取原告及被告的表述,所以对此案件做出了并不十分合理的判决。而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该案件存在着适用于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这说明,我国关于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等方面的法律解释还不够完善。因此我国应加强这方面法律内容的建设。
——实践部谭家星
齐玉苓案件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第一案”,在此案件中通过侵犯姓名权最终侵犯了齐玉苓的受教育权,而最高院直接适用宪法作为民事审判依据的司法解释也引发广大争议,并最终以“被停止适用”为由而废止。这一做法其实已表明了最高院的态度,宪法目前仍不适宜在中国司法中直接适用。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不认同齐玉苓案件是宪法案件,因为其最终指向的是民事赔偿诉求,尽管牵扯到了受教育权的认定问题,实质是因民事侵权法中受教育权的立法空白只得向宪法寻求法律依据支撑。我的个人看法是,基于中国国情,宪法适用不可操之过急,宪法司法化这一提法暂不可行。宪法适用道路的背后,不可回避的本质问题是宪法中规定的中国分权体制,宪法解释权归全国人大所有,司法机关无权解释又谈何应用,其背后是司法权僭越分权机制的隐忧。同时,我国并未建立起违宪审查机制,司法机关也并无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权,宪法适用并未有足够正当性支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宪法最高法地位和权威的动摇,反之,宪法精神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应渗透到司法的各个领域,成为原则的指引,下位法应当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能直接援引宪法作裁判依据,但可做辅助判决理由,不失为体制下的突破尝试。中国宪法适用之路,应当结合国情,不可盲目急进。
——宣传部张婷婷
如果宪法作为具体的适用法律,那么司法机关必须拥有宪法的解释权,没有解释权便难以处理问题,无法使用,所以这也是司法机关的一种无奈,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我国的权力机构的设计原因。另外宪法司法化还有其他阻碍。宪法缺乏可操作性。宪法缺乏一般法律具有的假定、处理和制裁内容,所以涉及到一般法律无法解决的案件,就需要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会让法官很难处理,同时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
宪法在扮演着一个“纲领”和“宣言”的角色,从立宪开始一直如此,所以对宪法的司法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我国缺少宪法控诉制度,这样会使违宪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即使我们要喊着宪法司法化的口号,那么也无法对违宪行为进行控诉处理。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违宪的行为,上至国家机关,下至平民百姓,让执行中出现“以法凌宪”的现象也与此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这实质上否定了当事人可能对行政依据合宪与否质疑的诉讼。宪法不能司法化,宪法很容易成为一种摆设,国家根本大法反而发挥不了和他的纸面地位一样的作用,公民的基本权利侵害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对许多方面出现的违宪问题无法真正威慑和处理,“以法凌宪”也无法解决,所以我们要让宪法发挥作用,如果能对社会和司法产生推动而不是破坏,我们不妨考虑宪法的适用问题,让它不再是一种摆设。
——研究部张磊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除了发挥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总是难觅踪影。但宪法首先是法,法律应该能被实施,因此宪法应当从神坛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为民所用。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应该在公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发挥更大程度上的作用,而不应该作为神圣的理论束之高阁。“脱离实际生活的宪法只是纸上的宪法,其生命已经枯竭,价值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会对实际生活发生负面作用”。表面来看,“齐玉苓案件”纯粹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索偿案件,然而,在中国司法界产生了极大的回响,这是因为侵犯姓名权在中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它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加上长期以来,在中国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
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而最高人民法院于年8月13日为此案作出的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开创了以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先例,也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社会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的时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不能不谈到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围绕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依宪治国”方针的大背景,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有其积极的重要意义。虽然在年最高法院废止了对该案的批复,但不可否认的是实现宪法司法化是我国法制进程的必然发展趋势。
——实践部邹雨庭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体制之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所明确规定的宪法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权威的宪法解释权,而法院并无此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其所制定的法律不容其它国家机关提出合宪性质疑,应该一概被推定为“合宪”,“宪法不可诉”是几十年来中国法律界遵循的默认规则。
齐玉苓案件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齐玉苓案是在法院的民事庭判庭审理的。双方争议的焦点并不是在于宪法的某个规定如何理解的问题,也不涉及到民法和教育法是否违背宪法的问题。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民法上的许多权利,比如所有权和继承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都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民法上的其他权利只不过是这些基本权利的细化而已。本案原本可以直接援引教育法和民法通则判决,而不必要撇开教育法而造成宪法司法化的假象,宪法诉讼一定要在其他法律法规的保护手段用尽之后,才能进行。否则,将导致宪法诉讼的泛滥,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也就降格了。
——秘书处吴彦沐
我认为,就我国而言,宪法的地位的确是略显“尴尬”,一方面,它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不得与之相违背;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搁置”——不能被法院作为审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一定程度上没有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而我理想化的宪法的实施,是由两种解决纠纷机制组成的:一是通过违宪审查机制,解决宪法中的国家权力纠纷和国家权力侵害纠纷;二是通过宪法私法化的宪法诉讼方式,解决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以外的侵犯或两种公民宪法权利相冲突的私权纠纷。我们不妨借鉴外国的经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道路。
——秘书处辛玥颖
END
哪的白癜风医院权威治白癜风哪家医院好转载请注明:http://www.tengzhouzx.com/tzszy/3420664.html